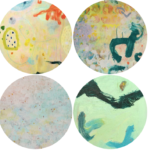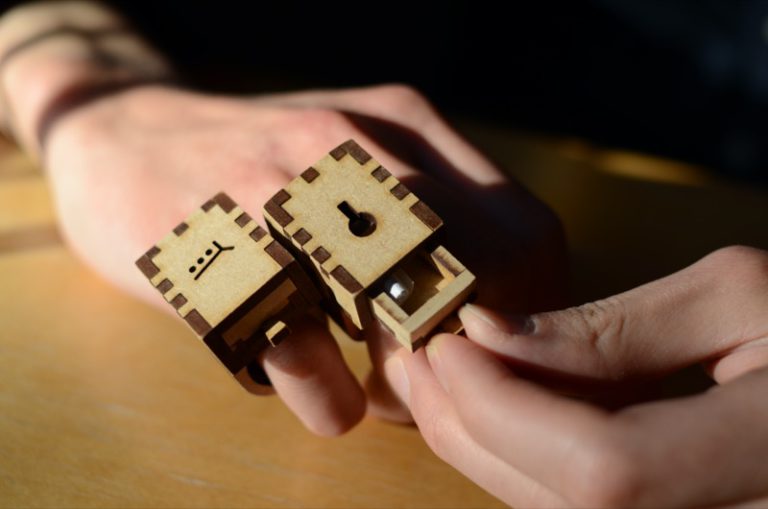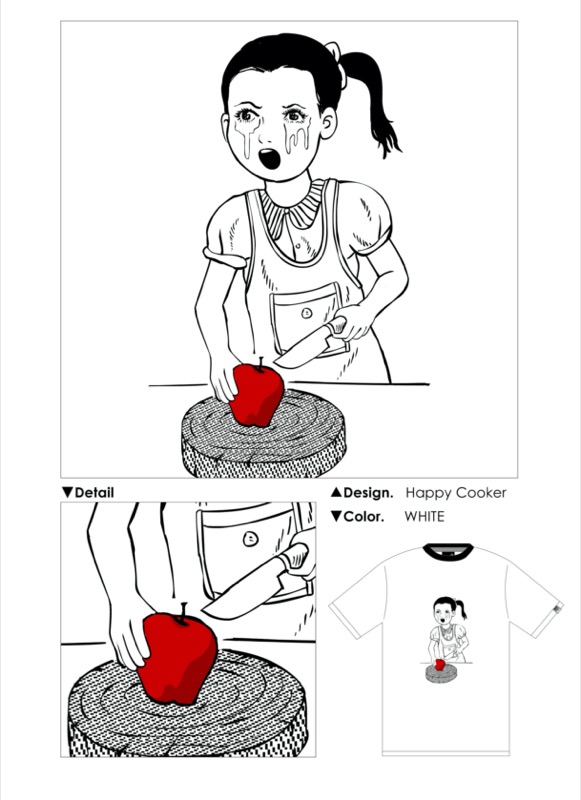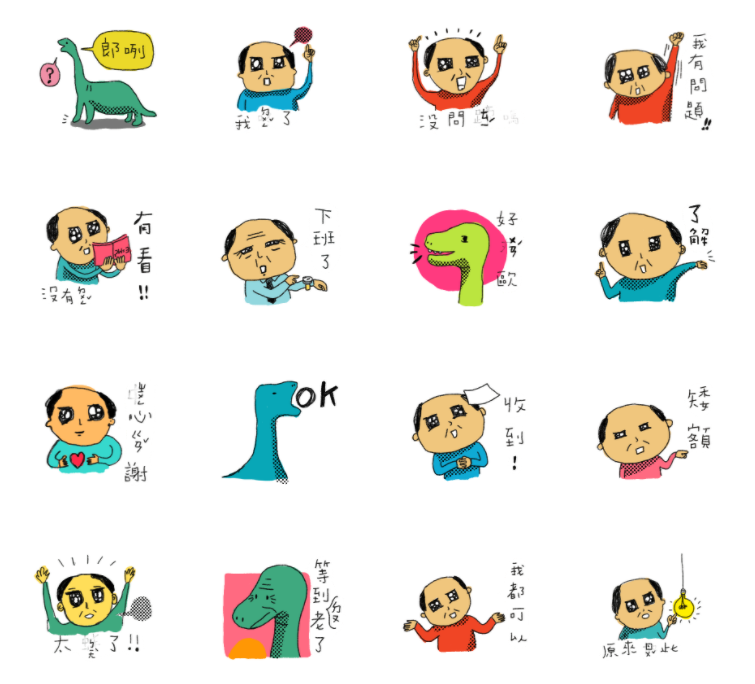應該有不少人認為藝術必須帶有某種刻意,才稱得上是藝術。
就算是刻意無刻意也算是一種刻意。
因此觀眾期待藝術家必須用語言文字解釋些自己的刻意,才算合法的藝術家。
所以當藝術家很辛苦呢,總是被當犯人般審判,被強迫要寫下些自白,不然就是騙子。
有好多年,想到要解釋自己的作品,就覺得很抗拒。不是因為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,要是有那麼單純就好了;而是總覺得只要對作品一說些什麼,整個作品就瞬間失去它的整體性,我一直不明白也說不出是為什麼。
直到很偶然的機會在一部經典裡找到了答案 — 語言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他無法”同時”詮釋一體兩面的東西。比如我說出「是」的當下就已經失去了詮釋「不是」的可能性,就算我說「是也不是」仍然在「是」和「不是」的意義中打轉。語言永遠在描述一種二元世界—非黑即白。
因此我對作品說出的任何話語,都是在減損直觀體驗的可能性。
然而那卻是我最珍視的部分。